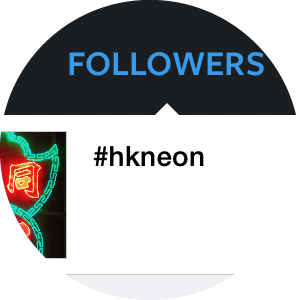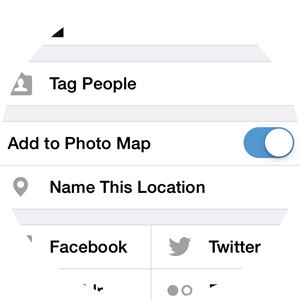(原文刊於 頭條日報)
西九M+辦的網上展覽「NEONSIGNS.HK探索霓虹」暫告一段落,至六月三十日為止,M+告知公開徵集霓虹照片共四千張,反應可謂相當熱烈。這是一次很好的網上展覽嘗試,集專家文章、訪談錄像與公眾參與;當然未來收藏的雞記麻雀館和森美餐廳招牌等如何以實體展示、如何繼續書寫、發掘、研究霓虹自身美學、與城市及現代化的關係,以及霓虹於不同藝術文本中的再現等,仍有待延續和深化。
作為一個文藝創作者,我個人對霓虹在文本中的再現或較敏感。早前替M+撰文時提到一些有關的香港文學小說、電影、歌曲,後者如上世紀八十年代達明一派的《今夜星光燦爛》,隔了二十多年來聽,竟沒有過時,卻似更切中當下情景。萬家燈火、燈光璀璨本是美好圖像,但華麗的城市淒迷從來不是絕然的漆黑不見五指,而是淡淡哀愁掩蓋於繁華幻象之下,所謂美好,脆弱得不禁手指一戳,即化成碎片。「請看一眼這個光輝都市/再奔馳/心裏猜疑/恐怕這個璀璨都市/光輝到此」,詞句延宕至今,竟成一份集體焦慮了。
近日媒體也流行把昔日金曲重播,置入當下社會情景,隔代輪迴又像重獲新生。如是者,我想起達明一派另還有兩首歌曲,一樣流灑著青春叛逆、城市夜色,也同樣將霓虹譜進詞中。一是《馬路天使》(達明一派不少歌名取自電影,此是一例),如《今夜星光燦爛》般一開始即以霓虹帶出:「叱咤於漆黑街中,身軀傲然隨處碰,在眼中,在半空,是赤色的霓虹」;另一是《迷惘夜車》:「劃過於千重霓虹,夜幕在默然流動,我已覺冰冷又凍,在眼中奔流無窮,是寂寞盡情愚弄,理智已失了自控,我亂碰亂碰亂碰亂碰亂碰卻一空」,迷走青春與城市之間,如此樂音,於今好像不可復聞。三首歌曲,都出於陳少琪之手;詞人擅寫城市空間、景觀,將遊蕩意識與城市感性摻和,可見一斑。尤其是城市的夜,愈夜愈美麗,愈快樂愈墮落,一點點的頹廢感,青春期所獨有的,那時少年還未成「早餐派」。
文學不僅在一本本文學作品中,也擴溢於街角、流行曲之中。如果說「詩歌同源」,在此也提提幾首詩作,聊作補遺。如果說上世紀五十年代曹聚仁《酒店》將慾望霓虹寫進小說中,五十年代,霓虹現身香港詩作,有現代詩人馬博良(馬朗)的《北角之夜》。詩的開首是這樣的:「最後一列的電車落寞地駛過後/遠處交叉路口的小紅燈熄了/但是一絮一絮濡濕了的凝固的霓虹/沾染了眼和眼之間矇矓的視覺」;往後詩段出現了「零落急促的舞孃們」,其纖足「登登聲踏破了那邊捲舌的夜歌」,有聲音,也有顏色和溫度:「玄色在燈影裏慢慢成熟」;尋常如北角,霓虹一樣流竄著一股慾望暗流,帶著沉醉和勾引。另有意思的是,隔了近半世紀,另一不同世代的詩人陳滅以同一詩題隔代回應,其《北角之夜》有詞句如下:「火燒的霓虹招牌接續後退,在窗外/迎來了「現在」,現在忽而狂笑絕倒/忽而因一句話靜默,收斂了歡聲/朋友幽幽嗚咽,那是突發的哀音/還是自從前延續至今?」電車尚在,霓虹卻不往後退,北角許亦非昔日的北角了。此詩寫於二○○四年,同一年,且以時間作蒙太奇縫接,也斯寫下了《城市風景》:「城市總有霓虹的橙色/哪裏有隱秘的訊息/只可惜你戴起了口罩/聽不清楚是不是你在說話」;耀目霓虹配上白色口罩,城市的顯與隱盡收其間,沙士的畫面又復喚起。
文︰潘國靈